七一文学丨摇曳在树上的童年时光(上)丨徐成文专栏
文章来源:七一客户端发布时间:2021-07-20 21:56:41
与命运一道,我降生在荒僻的农村。睁眼的第一天,满眼的树木映入我的眼帘。
树木,与我的童年缠缠绵绵,在那些晦暗的日子,时不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孩子,虽然没有城里孩子那些令人艳羡的“高大上”的玩具,但广阔的农村也蕴含着无穷的乐趣。
院子后面的庄稼地长着无数的桐子树,我们的“瞎子摸鱼”游戏就在桐子树上完成。游戏规则极其简单:大伙首先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选出第一个摸“鱼”的人,我们称这人为“瞎子”,其余被摸的人称为“鱼”。大伙将“瞎子”的眼睛蒙住,“鱼”们就在那棵大桐子树上“游来游去”。游戏特别强调,任何人不得离开那棵桐子树,否则将会受到重罚。
“瞎子”感觉大伙藏好后,会问一声:“行了不?”大伙异口同声:“行了!”“瞎子”就在完全“失明”的情况下,顺着树丫到处去摸“鱼”,而“鱼”们则尽可能不让“瞎子”摸到。所以,当“瞎子”来临时,“鱼”们总是从这个丫杈跑到那个丫杈。也有顽皮的“鱼”,总是躲在“瞎子”的后面,用手指敲一下“瞎子”的后背或者脑袋,希望“瞎子”去摸他。而当“瞎子”转过身去摸他时,他却像个猴子一样蹿到另一根丫杈上去了。
被“摸”到的“鱼”往往是胆子小的。“瞎子”往往凭感觉断定某一丫杈上有“鱼”,就来个顺藤摸瓜,一直沿着那个丫杈摸上去。胆小的“鱼”既不敢跃到旁边的丫杈去,又担心丫杈要断掉,所以当“瞎子”逼近时就只有“束手就擒”。被摸到的“鱼”就充当第二个“瞎子”开始摸鱼,依次往下。
这种游戏没有什么奖惩,大伙在一起图个好玩。只要听见哪家的大人在呼喊孩子的乳名,我们便迅速从树上跳下来,背起背篓各自回家。
今天看来,“瞎子摸鱼”十分危险。记得有一次,我们在火地湾的一棵桐子树上玩这游戏,由于玩的人多,一根丫杈上聚集了好几个人,丫杈承受不了重荷就断了,几个孩子掉了下来,好在只是受了点轻伤。大人们生怕孩子们有个三长两短,家家户户都不再允许孩子玩“瞎子摸鱼”,我们只得偶尔偷偷玩。
鲁迅小时候在三味书屋后面的园子寻蝉蜕,而我的童年则在房屋对面的那片杂树林子里寻鸟巢。当繁花似锦的时候,我们脱去厚重的棉衣,显露出矫健的身姿——这个季节最适宜爬树。
为了一颗诱人的水果糖,我和玩伴成忠打赌看谁先爬到同一高度的树上。本是一次打赌的嬉戏,我们却有了重大发现:两棵白蜡树上均有鸟巢,但没有鸟蛋。
鸟蛋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美味佳肴。我们不打无准备的仗,先叫年纪最小且没有上学的玩伴成阳躲在树下观察,摸清楚是什么鸟,因为不同鸟类的鸟蛋大小不一。我们还给他吩咐了另一项任务:摸清楚那片林子里还有没有鸟巢。
一周后,成阳跑到我这里汇报“战报”——他看见有几只斑鸠经常飞入树林,还了解到有一棵树上有麻雀窝。我是院子里的爬树能手,人长得干瘪,与猴子无异,他们戏称我为“猴子”。我快捷爬到那个斑鸠窝,细细打量窝穴,发现斑鸠正在加紧筑窝。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一旦斑鸠筑窝完毕,很快就会下蛋孵小斑鸠。我们得在斑鸠孵化小斑鸠之前将蛋取下。
第二个周末,我再次爬上树,三个白花花的斑鸠蛋卧在窝里,我小心翼翼地将斑鸠蛋揣在衣服口袋里。下树的时候,不再是一梭而下,我放缓了速度,生怕枝丫碰到了斑鸠蛋。
首战告捷。大伙围着斑鸠蛋爱不释手,东摸摸西握握。蛋少人多,分配成了难题。
“成阳不是说其它树上有麻雀窝吗?”有人提议。
我刚从高树上下来,消耗了不少体力。于是大伙推荐成龙爬那棵矮小的白蜡树,取下麻雀蛋。成龙身子微胖,但大伙期盼地看着他,他只得硬着头皮往上爬。
一支烟的工夫,成龙也取下五颗麻雀蛋。斑鸠蛋与麻雀蛋大小不一,分配又侵扰着我们。大伙七嘴八舌之际,倒完猪食的“老大”成奎来到,大伙最听他的。他将“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到底,我、成龙和成阳功劳最大,自然分得大个的斑鸠蛋,其余的分到小的麻雀蛋。
后来,随着年龄增大、文化增多,我们没有太多空闲时间,加之懂得鸟类是我们人类的朋友的道理,自然很少再去上树摸鸟蛋。那些摇曳在树上的童年时光,成了留存心间的记忆。
(作者系中学高级教师,重庆市万州区作协会员)
责任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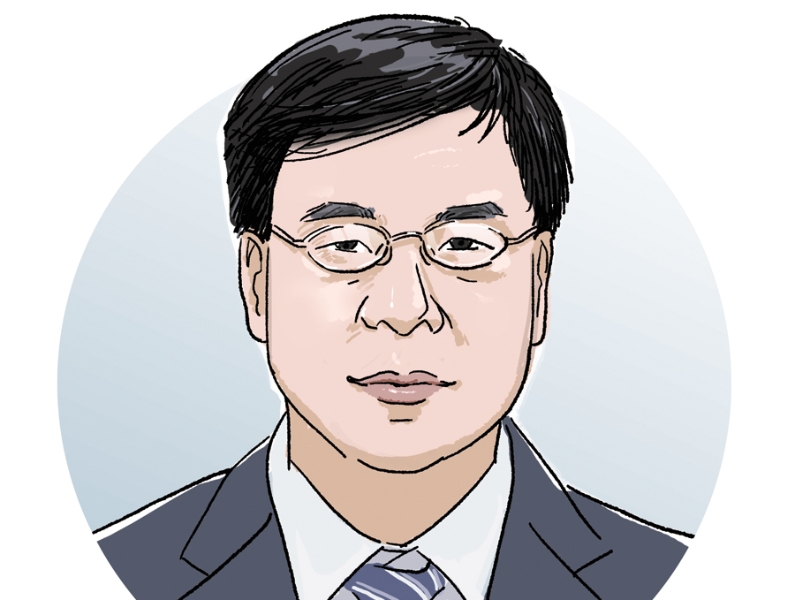
 原创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