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文学|母亲的顶针|乔加林专栏
文章来源:七一客户端发布时间:2022-10-25 15:18:3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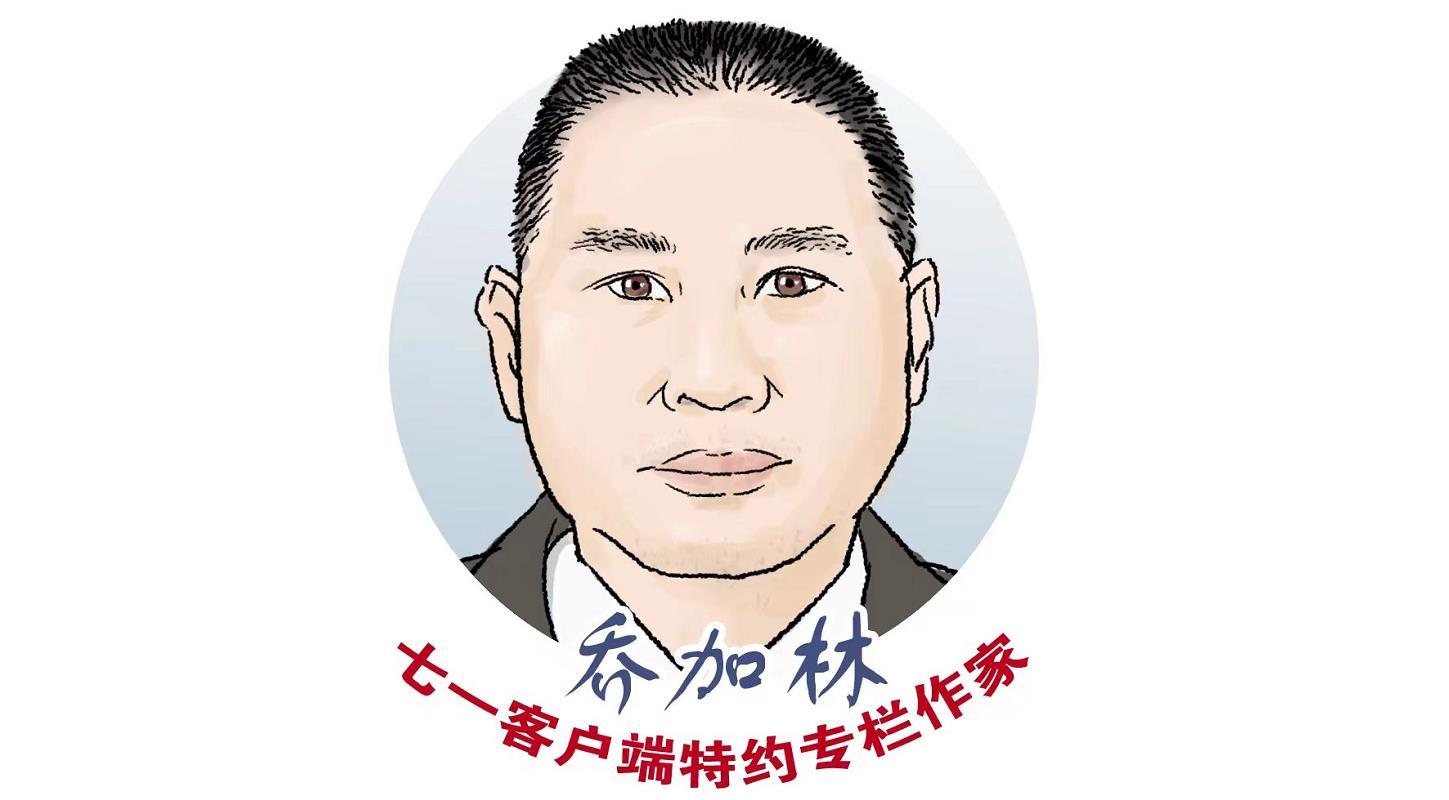
顶针,是20世纪70年代,农村妇女普遍的家庭缝纫用品。顶针,它是一个金属箍,有铝质的,也有铜质的,厚度大约一毫米,宽有两厘米,外侧布满密密麻麻而又排列有序的凹点。做针线活时,把它戴在右手中指上部的两个关节中间,穿了线的针鼻子顶住这些凹点,既减轻了手的劳动强度,也提高了缝制速度。
说起顶针,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比较陌生了。顶针和戒指差不多,但它不像戒指那样受人青睐,它只是用于缝补衣服的工具。
在我小时候,就总能看见母亲使用它,那时家里很穷。全家人的衣服鞋袜,还有我和姐姐背的书包都是母亲用这小小的顶针儿,一针一线地缝出来的。
秋冬时节,是母亲最忙的时候,无论白天和黑夜,都能看到她在赶制过冬的棉鞋、棉衣,尤其是棉鞋,厚厚的用浆糊粘贴的一层层坚硬的布拷子,首先得用锥子锥成小眼,再一针一线地穿透,由于布拷厚度很大,就必须用顶针来顶着针尾将针送过厚层,这就必须用力。白天还好,日光充足,屋子比较敞亮,费点力气就可以了,而到了晚上,那境况就完全不同,昏暗的煤油灯下母亲的脸几乎紧紧地贴到了煤油灯上,一针一线地缝补着旧衣裳。
在80年代以前,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穿的鞋子都是自家做的布鞋。那时候,我们的穿着是什么状况?就是当时最为流行的顺口溜足以证实: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可见一件衣服要穿九年!穿破了的旧衣服,还是舍不得丢弃,留着来改小一点的衣服,到最后母亲就会用来糊拷子留着做鞋帮与鞋底。
那时候,母亲在白天忙完农活后,晚上经常会把家里一些不能再穿的破烂衣服,洗净,撕开,然后找太阳强的好天气在桌子面上用浆糊一层层粘起来,铺平,粘满一层后再粘第二层,一般不超过五层。在太阳底下晒,晒干了再按照各人脚的尺码大小剪鞋样,把那些晒干的布再用浆糊层层贴起来,照着鞋样把它剪好。在做鞋底前,母亲把鞋底样子压在袼褙上拿剪子开鞋底。开出的鞋底用“白花旗”条子沿完边子,在纳鞋底之前。还要准备一个“针锥”和“顶针”,因为鞋底太厚,穿针要很大的力气,必须用这两个工具才能完成。针锥先把鞋底锥一个小洞,再用顶针把带线的针顶过去。当针尖穿过鞋底遇到阻力时,戴顶针的手指往前用力一顶,就穿过去了。有时还要准备一点蜡,在针上和线上抹一下,起到润滑作用。针穿过去了,自然也带了线一起穿了过去,还得用手使劲拉线,拉得越紧,鞋底就越结实,由于拉线得直接用手,还得用力,纳完一双鞋底,母亲的右手中指和食指就伤出很多口子了。
纳鞋底用的大都是自家用棉花拧成的棉线,每纳一针鞋底,母亲都会把针在头发上蹭一下,引过的棉线绕在锥子把儿上使劲儿地拽几下,那密密麻麻的针脚就留在鞋底上了。针脚的大小决定做出的鞋底是否耐磨。母亲总是把鞋底纳得很密,鞋底纳稀了,鞋帮不等穿坏,鞋底会先磨出洞来。
纳鞋底是个慢功夫,时间一长,手指会酸痛,眼睛会发花。有时母亲手发麻不小心还会扎着自己手指。已记不清多少个日日夜夜,我是望着鞋底上密密匝匝的小针脚和母亲那疲倦的眼睛而渐渐地进入梦乡的。母亲纳鞋底那熟悉的棉线抽动的嗤嗤声,现在还时常回响在我的耳畔。
鞋底纳好了就开始做鞋帮,男同志的鞋帮脚面部分,要剪成倒“几”形,两边连上“松紧布”,这样做成的鞋帮容易穿上脚。老家人都叫松紧鞋。女同志的鞋帮通常都是剪成“n”,老家人都叫大口鞋。把“缉”好的鞋帮与鞋底儿组合到一起,叫上鞋,上鞋是做布鞋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没个好手艺,鞋帮儿就会上偏,不仅穿着难看还不舒服。因此,母亲每上一针都要比量一下,认真对待每一针,避免白搭工夫最后前功尽弃。母亲做鞋的细心和耐心是出了名的,她做出的鞋不仅穿着舒服,而且特别美观。
在那艰苦的日子里,一家五口人的衣服、鞋袜、被褥都是母亲一人完成的,而使用顶针最多的地方就是做鞋和套被褥。做被褥相对轻松一些,因为被褥厚实,使用的针较长,更需要顶针了,不过力气不用太大。母亲左手在上面压住被褥,戴着顶针的右手在下面顶住长长的缝衣针,很轻松的做完了一床又一床的被褥,使我们在漫长的冬天里没有挨过冷,受过冻。
漆黑的乡村夜晚,小小的煤油灯光亮,真是难为了母亲。有时半夜醒来,发现母亲还在挑灯夜战,在灯光的影子下,母亲把做衣服的针放进头发里,反复摩擦几次,使针脚更加顺畅。
改革开放后,村里终于通上了电。有电了,母亲白天干完的家务活,晚上就可以在明亮的灯光下缝制衣服或鞋子,在明亮的电灯下,母亲缝制衣服的速度也快了许多。
80年代末,我参军入伍。母亲考虑我的汗脚很重,缝制了一双黑色灯芯绒布鞋寄到部队,大大缓解了我常年穿部队军用胶鞋带来的苦恼。
母亲缝制的灯芯绒布鞋,在当时很时髦,褐色塑料底,用黑色迪卡布缝制两条压边线,很是精巧,鞋面上口用“五眼”压制,能系鞋带。穿在脚上,系紧鞋带很舒服。母亲还特意缝制了两双鞋垫放在黑色灯芯绒布鞋里。宿舍里的战友都以为是在商店里买来的新鞋,不相信这是母亲亲手缝制的,纷纷夸奖母亲有一双巧手。
在部队期间,虽然没有机会天天穿布鞋,但在休息、上街或出差时便与军用胶鞋替换穿用。有时,躺在床铺上,一想到母亲缝制的那双灯芯绒布鞋,心里就暖暖的。
岁月沧桑,年轮更替。在不知不觉中,母亲已经八十多岁了,脑梗导致半边身子瘫痪,再也不能为我们缝补衣裳和做鞋了。每当看见“顶针”,就会想起母亲的辛劳;每当想起母亲的顶针,就会想起儿时围坐在母亲身边,看着母亲一针一线为我们缝制衣裤、纳鞋底做鞋的一幕幕场景。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中国散文学会、中国青年作家协会会员;华夏精短文学会江苏分会副会长)

编辑:王耀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