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文学·胡杉专栏│许老师(一)
文章来源:七一客户端发布时间:2023-01-31 13:48:56
我中学阶段没学过历史,考大学考了4年,靠扩招读了个专科。最不堪提及的高考成绩是历史,第一年考了17分,第4年也没考到40分,4次高考的历史成绩合计不过上百分。
读专科期间常琢磨毕业以后自学什么,一想这个问题,挥之不去的就是历史。
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我的高中母校做初中语文教师,于是一边工作一边自学历史和外语。一年多以后,我对历史产生了些许兴趣,想报考历史专业的研究生。这消息传开,同事们莫不惊诧。当时的校长还是我学生时代的校长,老领导说了一个词,精准地概括了我的冲动:魔想。
为这个魔想苦缠苦拼了5年,先后考了3次,竟然有机会进入复试了。我选的学校是我们省内一所不在省城的师范大学,专业是隋唐史。那个学校历史系只有一位李教授有资格带研究生,且当时还没有学位授予权。
李教授的指标是2人,4名考生参加复试,3名是李教授的学生,我是第4名。
主持面试的是导师李教授和副导师许老师,系里教学秘书在现场记录。
李教授在面试我时首先告诉我,我是专科毕业,不能算大学,没有考研究生的资格,何况我的专科还不是历史专业,因而只能算以同等学力报考。李教授在开场白中还说出“乡村学究”这个词。其实我不敢当,我确实生活在乡村,但哪有资格称“学究”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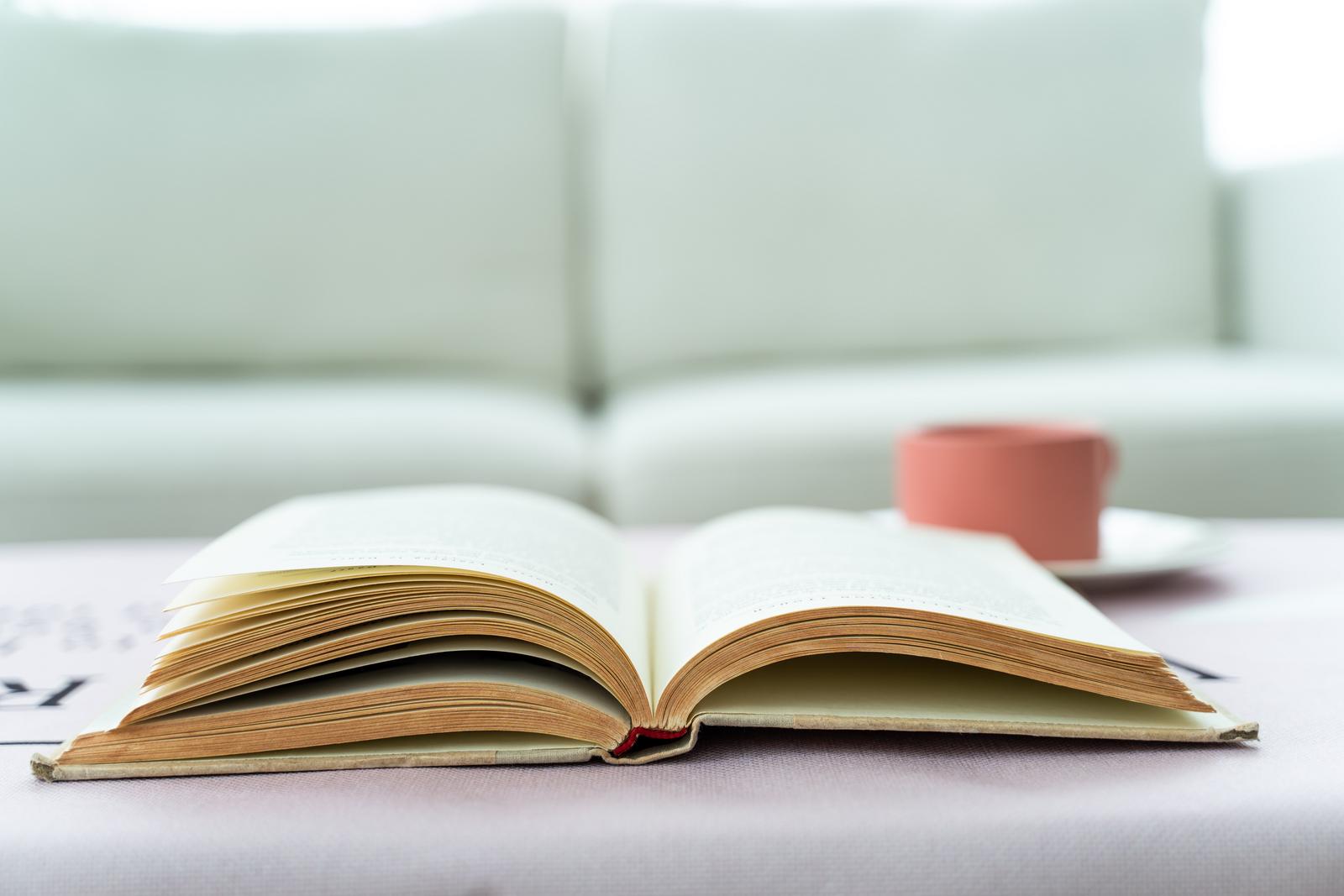
李教授举出许多专业书,问我读过没有。幸好,大部分我都读过。
李教授投来慈祥的笑容,问我读过两《唐书》和《资治通鉴》没有。
我答读过。
李教授问我读过《四库全书》没有。
我答没见过。
最出乎意外的是,在中国古代有没有辩证法这个问题上,话头赶话头,不知不觉和李教授产生了争议。更不意想的是,一直沉默的许老师却开口帮我说话。
李教授又问了隋唐史的一些问题缓和气氛,然后让我退下。
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出那栋楼,漫无目的地拐到一处僻静地,倚在树上,心里急速旋转着两个字:完了!
晚上,我不敢去见李教授,来了许老师的家,我想确切知道是败局,然后回我的乡村中学。
许老师告诉我:再努力吧。

我心里释然了。接到面试通知以来的希望,到此荡然无存,像做了一场梦。
许老师细致地垂询了我自学的情况,我如实回答。
许老师鼓励我说“是读了不少书”。
当时我还不知天高地厚,把自己聊以自慰的狂话狂妄地说给许老师:考不上就考不上吧,历史是可以自学的,我那学校的教务主任说,他在山大读书时,山大历史系有个童教授,童教授很厉害,也是自学的。
许老师眼睛一亮,盯着我看了许久:你的教务主任是山大历史系毕业?
我答是。
许老师:哪年毕业?
我答:1955年或者1956年。
许老师沉默许久,然后对我说:你的第二志愿是郑州一家大学的研究生班?
我答是。
许老师:我认识那个学校历史系的高教授,在一次北京颁奖活动中。我给高教授写封信,你去碰碰运气吧。
我说:谢谢您。
许老师坐在写字台前,在打了红竖格的宣纸信笺上,用毛笔一气呵成写下两页蝇头小楷。
到了郑州,找到高教授。高教授坦率地告诉我,不找他或许还有希望,找他就没戏了。
我绝望了。

回到我的乡村中学,见到本县一同考了3年的一位朋友,他被录取了,他为我可惜,他说他有个亲戚的亲戚于老师,在北京某教育机构,或许能在我的第二志愿学校找到熟人。
当时我身上有二十几块钱,我现在的老伴把全家的钱都找出来,共找了十几块钱给我,我接过来放进书桌的抽屉里。
第二天,我开启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远行——去北京。结果,我把抽屉里的钱忘在家里了。那时候火车票便宜,我身上的钱够我去北京——郑州——回家,只是吃饭住店的钱稍显紧张。
到北京的当天便见到了于先生,那天下雨,我被淋成落汤鸡,于先生同情我自学不易,转托北大一位田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
到郑州我见到负责招生的系主任,主任要我先住下,等几天面试了再回。
我心里升起一轮希望的红日,但难耐的是囊中羞涩。
我住进那个大学的地下室招待所里,数了数身上的钱,交了3天的住宿费,留足回家的车费,还有2块多。
我每天吃两个馒头和一包榨菜,那时候馒头是一毛钱一个。
等到第三天,我再也坚持不了了,因为我坐公交去火车站还需要钱呢。我给主任说我先回去,复试时再来。
我没回旅店,直接坐公交去了火车站。
火车上,我的邻座吃了烧鸡吃猪蹄,我默默怀念忘在旅店里的馒头和榨菜。此后三十年间我多次去郑州,每次都想念忘在那个大学旅店的馒头和榨菜。


编辑:石俊豪 熊冬梅 全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