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毅专栏 | 那些年,那些借书给我的老师
作者:潘玉毅
文章来源:七一客户端发布时间:2023-11-28 15:30:51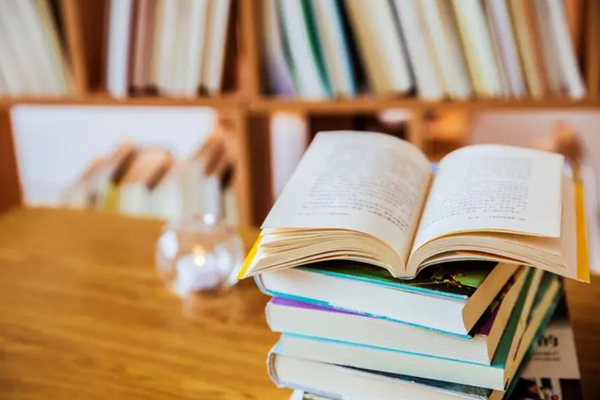

时光如流水,会冲刷掉很多记忆。但也有一些像小溪里的石头,稳稳地落在那里,仿佛扎下了根。读书时,借书给我的老师,就是我记忆河流里的那些石头。很多年以后,十件事情里有八九件都记不起来了,但是那些与书有关的故事,却依然清晰如昨。
第一个借书给我的老师应该是小学时候的潘长先老师。我们那个学校是村小,叫童家岙小学。老师之中大多数也来自本村,好几位都姓潘,学生在称呼的时候为了区分,管最年长的叫潘老师,其他几位则取他们名字里的其中一个字,遇到字相同、音相近的,再加上“大”或“小”,比如大英老师,英老师。而潘长先老师自然也被叫作“先老师”。先老师是从锦堂师范毕业的,在那个年代,也算是高材生了。偶然的机会,我和几个同学在先老师家的阁楼上发现了他读书时候留下的书籍,有《格林童话》,有《中国近代史》,还有《共产党宣言》等等。那个时候学校里没有专门的图书室,只有在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像变魔法似的拿来溜溜球、毽子、绳子和各类棋子,还会拿来一些书,其中以童话故事、科普读物和连环画居多,像《十万个为什么》《燕子李三》《神跤甄三》《七剑下天山》……相比于那些粗浅的读物,老师家阁楼上的藏书无疑更加丰富,也更加吸引我。于那时的我而言,小小的阁楼不亚于一个馆藏丰富的图书馆。
等到上了初中,从“童家岙”来到“龙南”,借书的对象就更多了。我问班主任金新华老师借过书,而且借过四本,一本是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一本是赵忠祥的《岁月随想》,一本是从维熙还是张洁的小说,书名记不得了,另一本则更模糊一些,只知道是青春小说,书名和作者皆已忘却。但这些书里的内容我分明还有印象,特别是当年阅读时的感受,至今仍觉真切。我也问教社会课的叶娟珍老师借过书,不过多是一些杂志,印象最深的是《文史知识》。通过这本杂志,我知道了古代围棋分成九品;知道了淝水之战背后的故事和那个“稳如老狗”、娴雅明断的谢安;知道了朱敦儒的《鹧鸪天》和别人嘲讽他的两句诗,从“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到“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这人生当真是无奈;还知道了一首词,大意是词人的一位朋友自学算命,算到自己命不久矣,于是散尽家财,潇洒人生,结果“死期”到了,人却没有死掉,只得典衣沽酒……值得一提的是,叶老师教课之余,偶尔也会写稿。有时杂志上就有她的文章,便觉得十分羡慕,心想自己哪一天也能像她一般发表就好了。那时候,作业、试卷是刻在蜡纸上用油墨印刷的,怕她不肯借书给我,我很心机地把这个活揽了过来,所以,那些年,同学们没少做我刻写的题目。我甚至还在周六上兴趣课的间隙,问实验室的管理员老师借过书。有一次,我们做“叶脉书签”的实验。我完成得较快,兴冲冲地准备打道回府,出门时,却见他拿着一本《悲惨世界》在实验室门口静静地看着。这本书我没看过,于是便凑上前同他套近乎。他自称是金老师的学生,与我算是师兄弟。有了这层关系,我便正大光明地从他手里把书顺走了。印象中,后来还问他借过《清平山堂话本》。这些书和借书给我的老师给我的初中岁月增添了无限乐趣。
如果说小学升初中是从村里来到镇上,那么初中升高中则是从镇上走到了市里。我就读的三山高中是一所新成立的学校,我们是首届学生。学校的校舍第一年在三北大街,后来又搬去了文二路。三山中学是有图书阅览室的,故而问老师借书的次数便少了,甚至还因为在课堂上看《水浒传》,被没收了一本去。当然,只是次数少了,并不是没有。比如从崔开军老师处我借过《唐诗鉴赏辞典》和《宋词鉴赏辞典》,特别是前一本,借了又还,还了又借。之所以如此折腾,是因为书很厚,许多典故我都没有听过,故而看得很慢。也不知道老师见我久不归还,心里是否会感到不快,本着“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原则,我反反复复借了好多次。后来,崔老师许是看出了我的顾虑,便对我说:“没关系,你慢慢看,看完了再还我。”于是,我的老毛病又犯了,觉得老师那么好,我也得帮点忙才行,自告奋勇帮着改了两回作文。如今想想,那时的字又丑,点评又不到位,纯属添乱。但回忆很美好。
今年是母校三山中学成立20周年,数月前,我翻改旧文,写了一篇《三山二十年,我们的爱不曾旧老》。前几日,又有同学应班主任龚老师要求,统计班里同学的信息,没来由地,我又想起了那段借书而读的时光,以及借书给我的高中老师,又从高中老师联想到以前的老师。想起时,我满心感激,因为是他们保留了我对于读书和学习的热情。由读而写,时至今日,依然不曾懈怠。


编辑:蒋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