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小玉专栏|爱是以一种持续的渴望与能量
作者:董小玉 安洁
文章来源:七一客户端发布时间:2024-07-09 20:29:35
《爱是什么》是西班牙哲学大师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著作,最早出版于1940年,2024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是一部以爱为主题结集而成的“爱的箴言”。自古以来,人类对“爱”的内涵追问不止、理解不一。加塞特则提供了一个哲学视角,他深挖不同阶段的爱,区分爱与欲望的不同,厘清爱的本质,指出爱会让人走出自我,走向被爱者——“爱是灵魂的离心行为”“爱者是生命里的勇者”。这样的“勇者之爱”指向了超越男女之情的更为广博的天地:爱艺术、爱科学、爱祖国……包括思想、信仰与意志力,它们有其共同的内核。为进一步体会“爱”的内核,西南大学师生展开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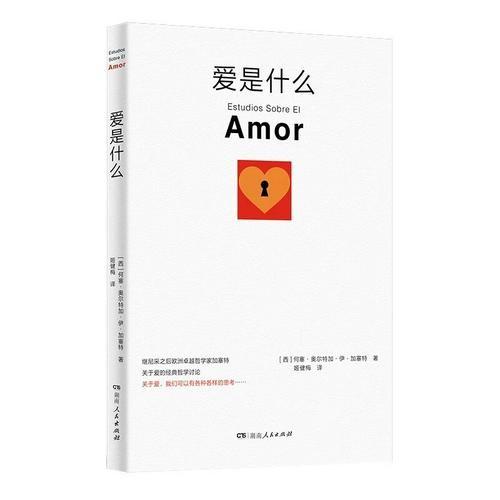
研究生安洁:“爱”是人类历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爱是一种涌动,是一道由心灵物质构成的光,是不断喷涌的泉水。奥古斯丁说:“爱是我的引力,不管将我拉向何方,它都牵引着我。”卢梭说:“生活就是爱。”拉康说:“爱不同于欲望,因为爱情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满足,而是为爱存在。”作为抽象的概念,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对爱的不同理解呢?
博士生导师董小玉:哲人们对爱的理解与自身所处的时代、经历和境遇无法分开——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指出:“爱是对美的企盼,美貌、智慧和美德都被讨论。”这是源于当时雅典城邦民主的历史背景,广泛的政治参与和公众辩论的氛围,让演讲与口才成为可以左右时局的武器,故而对智慧和美德的追寻成为柏拉图眼中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司汤达在《论爱情》中这样定义爱:“爱情在本质上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替对方添加了并不存在的完美。”这是受到19世纪欧洲盛行的悲观论影响,也囿于其自身“独角戏”爱情的悲伤经历。中国的爱的观念,也离不开社会文化与传统礼义的熏陶:元好问那句流传千古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与《孔雀东南飞》《牡丹亭》彼此印证。受到“生死相随”古典情义观与时代背景的共同影响,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试图说明爱情必要包含三种因素:唤起身体欲望、对新世界的渴望以及对崇高精神的向往。
由此观之,“爱”是一种主观的情愫,它的价值边界随着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而不断游移,后人不能指摘前人对爱之理解局限,当局者也无法高屋建瓴地洞悉当代爱之观念的全貌,因为爱的命题确实没有标准的完美答案。不过,纵观古今中外对爱之探讨,可以看出“爱”在大部分人眼中是一种正面的情感,有着积极的能量,这种情感可以激发人身上的美德,使其追求更美好的自我。
研究生安洁:加塞特在《爱是什么》中阐述了他对爱的理解,他认为爱所有的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关于世间千万种不同的爱是否有其共同之处、其本质为何,则是加塞特在本书中极力论证的话题。那么如何理解他眼中“爱的本质”?他对爱的定义又有什么独到之处?
博士生导师董小玉:关于认清“爱的本质”,加塞特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要想定义爱是什么,就要首先分辨爱不是什么。”他呼吁人们区分爱和欲望这两个常被人混淆的范畴。欲望是被动的,是出于主体的匮乏而滋生出的占有欲,一旦得到满足,欲望之火便会熄灭,被占有物也就随之弃去,但是实际上内在仍然匮乏,内心被无限的空虚所吞噬。但爱是主动的,是一种纯粹的情感行为,不同于思考、回忆、想象等认知行为,爱会产生欲望,但爱绝不是欲望本身。欲望是寻求“占有”的结果,而爱是主动的追寻。真正唤醒爱情的特质并非外形上的匀称或完美,而是某种生命形态的触动。
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中认为,真正的爱意味着尝试进入“他者的存在”,超越自身、超越自恋,意味着“从某一刻开始,从差异的观点来体验生活、体验世界”。爱正是以一种持续性的渴望与能量,在个体的生命中建构了一种全新而本不属于自己的时间节奏,用诗人的话来讲,爱是一种“艰难地想要持之以恒的欲望”。
加塞特与其他在西方哲学中探讨爱的学者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不局限于自身的生命体验,而是从与不同人群的谈话中、从历史的哲学反思中来论证爱的真谛。他先是观察男女之爱,再从中深思更广泛意义上的爱。谈及男女之爱,他剥离了许多附加其上、混淆视听的因素——例如两性之间不平等的职能与期待、社会规则对爱情对象选择的桎梏等等,如果排除这些干扰,那么爱情投射的选择应该是自然、纯粹的,揭露出个人最真实的基本性格,正如马克斯·舍勒所说:“谁把握了一个人的爱的秩序,谁就理解了这个人。”一个人基于个性选择了一个愿意为之投入热情的对象,并不惜牺牲自己的主体性,这便是爱燃烧的开始。
爱,是一个内涵广阔、意义深厚的概念,包括了走出自我、到达他者的过程,拥有的巨大力量绝不简单等同于“喜欢”“迷恋”“坠入情网”等。人们对爱津津乐道,而对其本质却理解不足,加塞特《爱是什么》用一篇篇短小睿智的对话录,为我们叩开了认识爱、继而认识自己的智慧之门。


编辑:别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