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诗学与文化的存续
——读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追忆》有感
作者:谭颖
文章来源:七一客户端发布时间:2025-07-24 08:35:14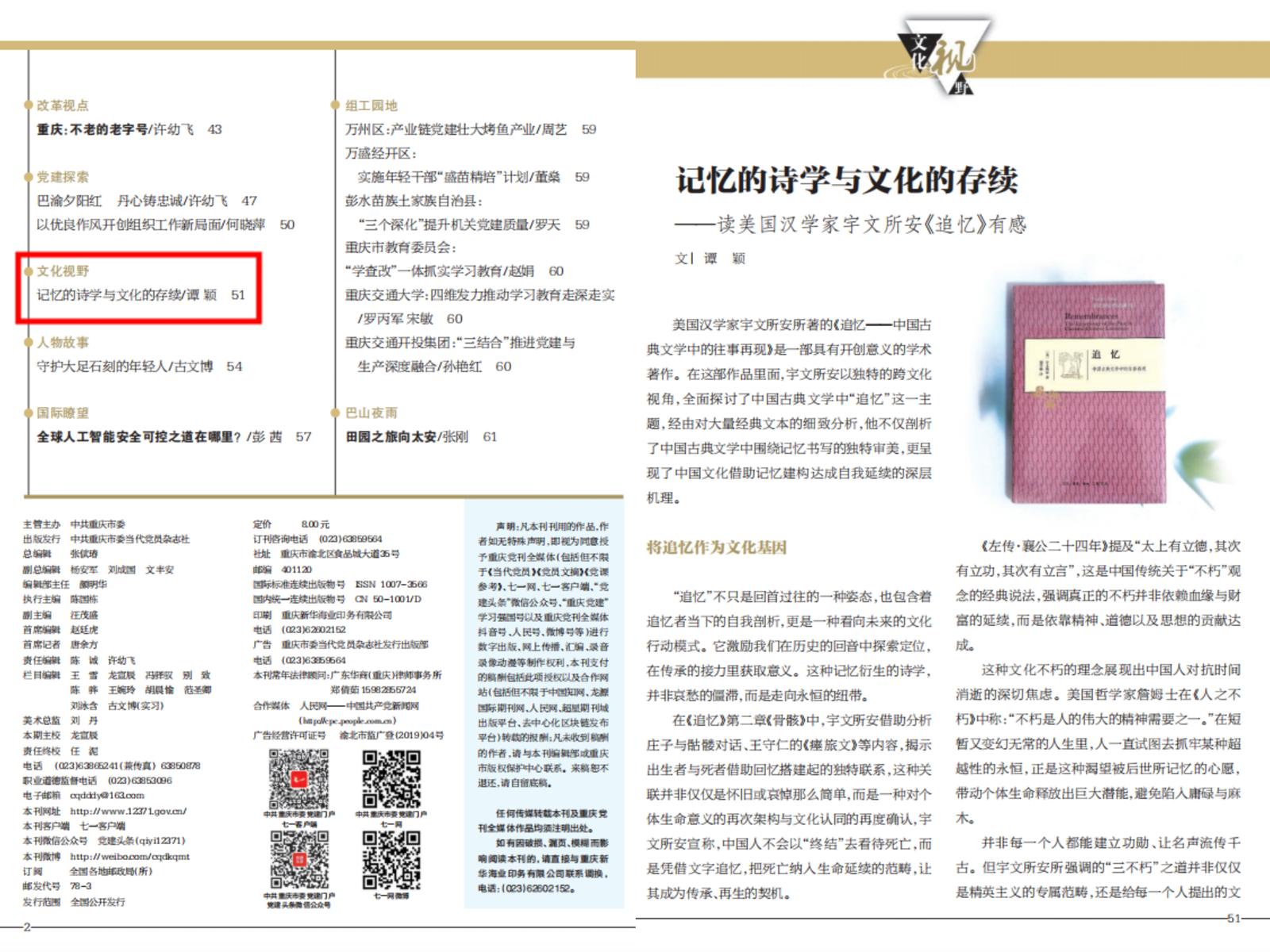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所著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是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著作。在这部作品里面,宇文所安以独特的跨文化视角,全面探讨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追忆”这一主题,经由对大量经典文本的细致分析,他不仅剖析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围绕记忆书写的独特审美,更呈现了中国文化借助记忆建构达成自我延续的深层机理。
将追忆作为文化基因
“追忆”不只是回首过往的一种姿态,也包含着追忆者当下的自我剖析,更是一种看向未来的文化行动模式。它激励我们在历史的回音中探索定位,在传承的接力里获取意义。这种记忆衍生的诗学,并非哀愁的僵滞,而是走向永恒的纽带。
在《追忆》第二章《骨骸》中,宇文所安借助分析庄子与骷髅对话、王守仁的《瘗旅文》等内容,揭示出生者与死者借助回忆搭建起的独特联系,这种关联并非仅仅是怀旧或哀悼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再次架构与文化认同的再度确认,宇文所安宣称,中国人不会以“终结”去看待死亡,而是凭借文字追忆,把死亡纳入生命延续的范畴,让其成为传承、再生的契机。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及“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这是中国传统关于“不朽”观念的经典说法,强调真正的不朽并非依赖血缘与财富的延续,而是依靠精神、道德以及思想的贡献达成。
这种文化不朽的理念展现出中国人对抗时间消逝的深切焦虑。美国哲学家詹姆士在《人之不朽》中称:“不朽是人的伟大的精神需要之一。”在短暂又变幻无常的人生里,人一直试图去抓牢某种超越性的永恒,正是这种渴望被后世所记忆的心愿,带动个体生命释放出巨大潜能,避免陷入庸碌与麻木。
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建立功勋、让名声流传千古。但宇文所安所强调的“三不朽”之道并非仅仅是精英主义的专属范畴,还是给每一个人提出的文化伦理吁求——就算最终会被历史遗弃,也应当尽量去立德、立功、立言,在有限生命里探求通向永恒的道路。
在这一维度之上,书写成为抵挡遗忘、留存个体记忆的重要手段。面对自然的浩瀚、生命的短暂以及身份的可消除性,文字承载着抵抗遗忘的力量,宇文所安利用庄子与骷髅的对话,不仅激起关于死亡的哲学思辨,还警示我们:正是回忆铺就了对现实的深层认知,而书写是这种认知的形式化呈现。
孔子所倡导的“述而不作”,并非是否定创造力,而是突出文化传承方面的伦理责任,文明的连贯延续,不是指每一代人都要去开拓全新世界,而在于每一代人都要把值得传承的思想、语言及经验保存起来并进行承载。
记忆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部分,是实现个体与集体联结的精神纽带。
对抗遗忘的文化实践
面对永恒的自然,人类的存在好像渺小又须臾。宇文所安认为,“寻常”一词在中国文化范畴内具有特殊含义,它不只象征着普通和平淡,更传达出个体特征被时间湮没的危险信号,这种“擦掉个体特性”的效应引发了深度的文化焦虑——人们所害怕的不只是死亡本身,更是死后被彻底淡忘的归宿,而这种焦虑造就了中国独特的书写文化,书写成为对抗自然遗忘的有效方式,使个体的生命可冲破时间的枷锁,在文化记忆中延展。
宇文所安对张岱《陶庵梦忆》的解读,属于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明朝覆灭后,张岱在国家覆灭、个人困窘的境遇里转向书写记忆,借此重建内在的精神架构。张岱书写记忆有两个维度:一方面是对过去盛世的追思,另一方面则是对未来进行架构。记忆于此处成为一种慰藉,属于对过去的怀念,也是对当下与未来实施架构的尝试。
张岱把往昔的繁华比作“一场大梦”,这不仅是情感范畴的忧思,更是对历史断裂以及个体身份破碎的深度反省。他于清代初年陷入极度贫困与失落境地,把书写用作“消遣”的途径,但这“消遣”绝不是轻浮的,而是有着一种沉痛的自我审视意识。他记录过去的欢乐逸事与风流时刻,来对自己一生的“罪与过”做回望与交代,其文字流露出极为强烈的负罪感与焦虑,他的书写好似一种自我设定的未来审判,在字里行间做精神上的“赎罪”。
从宇文所安的视角看,张岱是一种“人生如梦”的哲学视角,他把一生的经历看作梦境,正如张岱于《陶庵梦忆》中所写的:“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梦与现实、记忆与幻觉在他的叙述中相互穿插,界限模糊。他天天起身,在“清醒”时整理那些“梦中”的往日,而这些“醒着的梦”跟他真正的梦境没有区别,都来自内心深处情感和记忆的涌动。
张岱对这类记忆开展有意识的重构与转录,他不躲开梦和回忆的混乱感,反而以自己的联想与杂糅为傲,处于梦境与现实交错的状态里。《陶庵梦忆》形成了一种别样的记忆美学——堪称重访旧境的仪式,也是对偶然闪现的记忆片段的温柔眷恋,正如张岱所写:“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写作对他而言,不再是直接记录当下的现实,而是精神的返归,是在历史废墟里再次唤起人与世界的联结。
宇文所安由此点明,张岱的书写实践表现出的是中国文学里一种特殊的“追忆诗学”——它跟西方文学中以自我解构为目的的回忆书写不同,它是一种利用对过去的复述与想象,把个体重新嵌入文化与历史序列的举措。这种诗学并非躲开现实的胡言乱语,而是对混乱无序世界的一种重塑;不是陷入伤感的泥沼,而是通往未来的阶梯。
历史解释的双重维度
在剖析杜牧《赤壁》的时候,宇文所安阐明了中国历史叙述里自然因果与道德评价并置的独特结构。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一诗句,从表面看强调赤壁之战胜负受东风等自然条件影响,实则隐藏着对曹操不道义图谋的道德评判。这种叙事策略体现着中国传统历史观的双重逻辑:一是历史依从自然循环的决定论逻辑,二是历史又承载起道德的秩序,人的德行好坏左右命运的走向的逻辑。从宇文所安的视角看,这种既看重天时又突出人和的阐释方式,让历史不属纯粹的偶然范畴,也非单一的因果纽带,而是一种饱含文化意义和伦理暗示的叙事体系,赋予了事件教化意义和承载文化记忆的力量。
在鲍照写就的《芜城赋》里面,自然机制跟道德秩序并置的叙事模式表现得尤为突出——城市的兴衰可认为是自然周期产生的结果,也隐含有对人性弱点的道德指摘。宇文所安认为,这种双重解释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折中,而是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哲学——历史既遵照无情的自然规律,也昭示着“伦理报应”的逻辑。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归咎于人的“堕落”,也能理解为命运的完结,聚合成所谓的“道德历史”,这种模糊且繁复的解释架构,让文学作品里针对盛衰兴亡的书写往往带有伦理的含糊之处:所谓物极则衰,在事物发展到鼎盛后,大多难以逃避走向衰败。鲍照笔下芜城的命运正印证了这一点,它走向毁灭是因为自然规律,也归因于人心的贪求,体现出中国文学里对盛衰背后因果关联的深刻洞察。
就以南唐后主李煜为例,他的亡国之因可认为是沉湎于享受、自甘堕落等,还能看成是王朝衰弱、朝代更替的自然趋向。宇文所安认为,正是这种解释里的多重性与张力,赋予中国历史叙事别样的魅力。李煜的悲剧形象好似是道德失败的象征。处在这种多重叙事的氛围里,道德批判往往仅是一层薄薄的纱,掩映着历史的冷峻开展。基于这样的缘故,中国历史书写未落入单一的决定论范畴,而是在自然机制与道德逻辑之间维持着解释的开放状态及复杂状态,使历史文本饱含深层的思辨维度。
宇文所安在《追忆》里所披露的,不只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针往事的再现途径,更是一种极具当代价值的文化理念。在全球化与文化同质化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宇文所安通过对庄子、杜牧、王维、张岱等人所写文本进行深入剖析,道出中国传统“记忆诗学”蕴藏的创造性潜力——回忆不是对过去的机械照搬,而是一个依托当下、面向未来的文化实践阶段。这些文学作品把个人记忆与文化身份、历史感、现实关怀融为一体,说明了记忆怎样成为文明延续的“基因密码”。正如宇文所安所写,文化创新离不开对传统的深刻理解与重塑,在现今这个文化记忆持续碎片化的时代,《追忆》给出了一条可用的思考途径:唯有不停思索过去,我们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这部著作不只是文学研究的成果,更是一种关于文化自信与精神延续的哲学启发。
作者:四川外国语大学法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

编辑:王婉玲

